
梁羽生,原名:陳文統。1926年4月5日生於廣西蒙山縣。曾就讀廣州嶺南大學化學系和經濟系。並獲贈文學博士殊榮。
畢業之後,入香港《大公報》,和金庸一起任副刊編輯。以首篇《龍虎鬥京華》,開始了他新武俠小說的創作。憑藉著《萍蹤俠影》一舉成名之後,他竟然在短短的30年的創作生涯中,不僅創作出了35部驚世武俠小說,還著有回憶師友情意的散文集《筆花六照》、對聯集《名聯觀止》等。
他創作之豐,之廣,之快,是無以倫比的。之所以豐盛,是因為他勤奮;之所以廣泛,是因為他博學多才;之所以快捷,是因為他熬過了一個個不眠之夜。之所以他的作品倍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關注,我認為這跟他深厚的文學功底是分不開的。
在他病榻旁的小桌上,總放著《宋詞三百首祥析》、《唐詩選注》等幾本書。這兩本面目全非,破爛的實在有點不堪觸摸的唐詩宋詞,卻是他的最愛。每次去探望他,他總是要我隨意抽選幾首詩或幾個詞牌要他背誦。讓我驚奇不已的是,無論我挑選任何一首詩詞,他不僅都能隻字不拉的將整首詩或詞完整的背出來,還能準確無誤地告訴你,整首詩或詞是由多少個字組成的。其超強的記憶力和對詩詞歌賦的火熱情懷,使我這個遠遠不及的晚輩深感慚愧。
尤其是當他知道我離異單身時,竟然以我的名字小燕開頭,脫口成詩,用顫悠悠的手,一筆一畫的寫下了“小樓昨夜經風雨,燕子如今尚未還。”的詩句。梁老能瞬間出口成詩(而且是藏頭詩)的本領,著實讓我佩服。
當我問他,老年人最大的福氣是什麼時,他回答說:“老年人要擁有有三老才會幸福,第一,有老伴(比如我太太);第二,有老友(比如何與懷等等眾多老朋友);第三,有老本(沒有錢做老本,我就不能住在這裏啦)。”值得慶倖的是,這“三老”,梁老都擁有啦。
摘白:悉尼作協副會長張曉燕
梁羽生開創了武俠小說的一代新風,在此之前的舊武俠小說始終難登大雅之堂,隨著「新派武俠小說」的出現以及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龍、溫瑞安等一大批武俠小說大家的先後登台,讀者從最初的底層人士發展到社會各階層,並為廣大華語讀者追捧,一時風起雲湧,開創了武俠小說的一個新世紀。與金庸相比,梁羽生的作品受中國傳統詩詞、小說、歷史的影響更深。
對於「武俠」概念的界定,梁羽生的觀點是~武是一種手段,俠是真正目的,所以「以俠勝武」是梁氏的一個基本觀點。
梁羽生、金庸一直被並稱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重要代表人物,但是,兩人境遇並不相同,金庸的名聲和知名度遠在梁羽生之上。封筆之後的金庸,仍成為媒體的焦點,其作品也反覆被搬上電視;而梁羽生則退隱澳洲。
在同行中,梁羽生一直對金庸評價比較高。1994年,梁羽生就曾在雪梨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上謙虛地表示:『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,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,是今天在座的嘉賓金庸先生……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,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,包括寫作技巧在內,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。有人將他比作法國的大仲馬,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。』
摘自~自由電子報

1994梁羽生與金庸在雪梨作家節對弈
他生性平淡,不求功名,一生只在《大公報》及其副刊工作,編輯,撰述員。和曾經的同事金庸相比,普普通通,晚年沒有諸多榮譽頭銜,也甚少在內地曝光露面。
他自小浸染國學,四書五經,愛好詩詞。詞比詩好,武俠小說中篇章回目多用詩詞,堪稱一絕。他愛下棋,圍棋和象棋水準都不錯,可以同時應付幾人。除了小說、詩詞,棋評也寫得很妙。 他和金庸,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大旗。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,“金梁並稱,一時瑜亮 ”。
1966年,受人之邀,梁羽生署名“佟碩之”,寫了《金庸、梁羽生合論》,談到兩人的不同: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(中國式)的,而金庸則是現代的“洋才子”。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(包括詩詞、小說、歷史等等)的影響較深,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(包括電影)的影響較重。本是切中肯綮的比較,但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,左右對立,令他承受了莫大的壓力。30年後,又有文人曲解評論,認為此文有借金庸標榜自己之嫌,從而引發一段金梁公案。但任憑世人如何揣度,梁羽生和金庸,在不同場合都表示過,他們是好朋友。其實,孰優孰劣,只是庸人所想,缺了任何一人,武俠世界怎能有如此的絢爛?
自1987年移居澳洲,梁羽生過上了閒雲野鶴的日子,讀書下棋,鑽研對聯,偶爾回香港看看。2004年12月,他回來,小住一月,多方會友。20日,記者在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酒店見到了這位80高齡赫赫有名的武俠小說大家。
戴著一副方框老花眼鏡,趿著黑色皮拖鞋,雖已白髮蒼蒼,但精神極佳。興之所至,他說話滔滔不絕,扯到歷史更是剎不住腳。鄉音難改,聽不懂時,他拿起筆,在紙上寫下漢字,有時還夾雜一些英文單詞。半邊牙齒掉落,說話好像有些漏風,但聲音洪亮,高興時音量突然提高八度,笑聲盪漾在房間的每個角落,害得在隔壁臥室的梁老太太特意走出來,不滿意地指指:又聲音這麼大,但他毫不介意。
在一旁作陪的香港天地圖書副總孫立川先生,不斷提醒他喝水,又不時暗示我時間不多,因為晚上已和金庸約好一起吃飯,現在不能讓他太興奮。但梁羽生不管,想說就說,擔心可能有所忌諱的金梁話題,也照談不誤,原定一個小時的訪問延長了一倍。
對文學,對歷史,梁羽生懷著真興趣,經典的,最新的,他都看,“90歲的我看,19歲的我也看”。講起來,一連串的名字從他口中蹦出,中國的,錢鐘書、陳寅恪、沈從文、王蒙、余傑,西方的,卡夫卡、薩特、達達派、野獸派、存在主義。去年諾貝爾獎文學獎獲得者耶利內克的《鋼琴教師》,也看過,“這麼另類的文學能得獎,我年紀大了,關於性的,不去評論。”
這次回來,他剛剛榮獲嶺南大學榮譽博士學位。從一個紅色布袋裏,掏出一疊收拾整齊的報紙,翻到那一張《大公報》,指給我看,一起獲獎的4個人,這是誰,這是誰。說到以前的歷史老師簡又文的那塊隋代碑文,他立馬起身到小書房裏找給我看。說到數學,他說,我現在就可以給您開立方,精神頭十足。
採訪時,孫先生拿出一幅題字——“梁羽生文庫”,是國學大師饒宗頤的筆墨,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梁羽生文庫而題。梁羽生大聲叫好,開玩笑說“對著老師的字,可以養顏”。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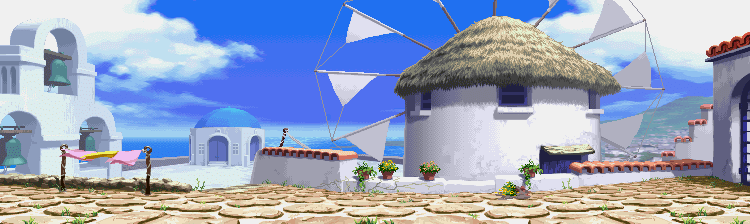


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